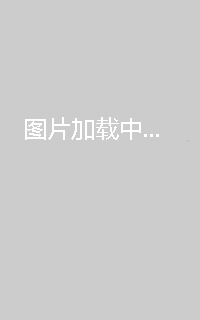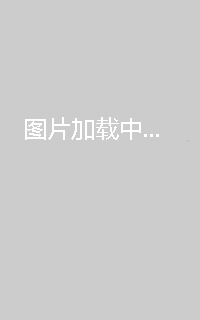剧情:
《多甫拉托夫》讲述了俄国作家谢尔盖(Dovlatov)在1971年时的四天生活。当时,Dov[展开]
《多甫拉托夫》讲述了俄国作家谢尔盖(Dovlatov)在1971年时的四天生活。当时,Dovlatov已经相当积极地在写小说了,但却没有在任何苏联杂志上出版。在这四天里,主人公最终卷入了各种事件当中,其中每一个都使他得出一个结论,即作为一个作家,要走自己的路,不要听从任何人的劝告。矛盾的交织循环、与布罗斯基的对话、列宁格勒的世俗生活,、西贡咖啡馆、大剧院的全盛时期、lenfilm工作室……这一切使《多甫拉托夫》不仅是一部传记电影,也是一个时代的写照
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小阿列克谢·日耳曼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杰出艺术成就奖叶连娜·奥科普娜娅多甫拉托夫电影网友评论:6/10。小日耳曼塔建起的政治讽韵和时代珞印布满大大小小的角落,游荡过街景的士兵和载着宣传画的拖车,还有最荒谎的一笔是暗示波兰团结运动的船厂拍摄场地,扮演托尔斯泰、普希金等文学巨匠的群演,参与采访满口积极工作的刻板回答,这个荒无且气候现象永远是云、雾和风的创作土壤,与当局要求撰写美化社会、塑造革命英雄的报道形成鲜明讽刺,多甫拉托失的生活比普通人的日常更加被无趣和黑色幽默所包围,例如把一个爱情幻灭写不出诗的石油工人拉到化妆舞会,或者送酒讨好一个误认为是作协大人物的尿道医生,时不时假装秘密警察让不醒酒的小贩纪录买禁书的人员名单,他常驻足出门框外,象征无法融入的距离感,从中汲取惰懒的虚无主义思考,漫步于一个不为钱和名誉只为传递真相的文人黄金时代。在斯大林时期,布尔加科夫无法发表作品,最后他直接给斯大林打电话说,“要么给我一份工作,要么把我枪毙”,最后斯大林没枪毙他而是给了他一份莫斯科某剧院的杂役工作。如今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世界公认的杰作。捷克的赫拉巴尔某段时间内也无法发表作品,身为法学博士,却干着底层的工作(打包工,钢铁厂工人,剧院杂役等等),他说他为了写出《过于喧嚣的孤独》而活着。决定作家能否发表作品的不是某个人,不是作协(在那时的俄罗斯,作协实在是个荒诞的存在,现在在中国也是),而是作家自己的文字以及读者认同。还有一种情况:不论发表与否,作家一直在写作(艾米丽·迪金森,佩索阿)。可如果不能发表没有读者,作家的写作是否还有意义?要去读谢尔盖·多甫拉托夫的小说。非常差。拍的不是多甫拉托夫,而是导演yy下的一个极权体制下的异见作家的四天。而且关于苏联基本的一些服化道都搞错。imdb第一条影评说的很好,多甫拉托夫不是索尔仁尼琴,他没有跟体制作斗争,他安安稳稳地活在体制里面,通过合法的手段移民美国。但是我觉得他的作品比索尔仁尼琴一更有力量,更humane。我觉得这才是多弗拉托夫的魅力所在。不抗争且说实话的气质。这种气质非常sutle,没有生活中极权体制下的人很难理解,但即使在极权体制下生活过的人也不是全都能理解。不带有任何预设立场地真实的描述人的生活与极权的关系,需要天赋和勇气。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得了这份天赋和勇气的。3.5,比起为革命斗士立传,更像是对存在主义的反证,因此叙事没有侧重于谢尔盖,抑或他身边那群失意的文学青年,而是近乎虚焦的背景:列宁像,铁皮船,浓雾氤氲的街道,以繁多符号勾连起一个极权倾轧、理想主义式微的昨日世界,从构图,转场到幽灵般的长镜头,调度技巧释放于无形,恰如这片土地上举世闻名,却被迫噤声或流亡的面孔,时间的飞逝了无意义,只是平添在铁幕下行进的乏力感。相较于在政治背景上飘忽几笔的《盛夏》,其间的萧瑟沉郁、对宿命感的传达更甚。不过,部分台词和心理描写还是偏弱,文本中静置的诗意过于散碎,没能朝前流动起来,人物间的镜像设置也略显单调。我是真的很希望自己懂一点俄语,好能从语言的细节里分辨出哪些是宣言式的权力话语,哪些是刺人也刺己的苦涩讽刺,哪些是真实的情感释放。不过我猜小日耳曼的风格确是在取消这些细微的区别。带着柔光效果的长镜头滑过一个又一个场景,好像是在发梦,又像是在带着感伤而缅怀。这和多甫拉托夫真实生活里的艰难大相径庭。不得志的艺术家哪里都有,可影片如此寡淡如此间离的处理方式让他的挣扎既不像西西弗斯般富有存在主义色彩,也没有抗争式的愤怒,只剩下一些磨平了的苦涩感,放在嘴里如同嚼蜡。说不定这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时代精神:一种麻痹了的宿醉感。如果从宏观角度把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归类为俄国文学的话,加上高尔基,屠格涅夫,契诃夫,也算读过几本。无论是沙俄,苏俄,苏联,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文学就像其国土一样“著作等身”。文学巨擘也是层出不穷。如果说托翁和陀翁一直是不敢触及的彼岸是因为其历史凝炼的恢宏,那诸如《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我们》,《生存与命运》则更是加持了历史悲剧的共鸣。他们有没有“伤痕文学”一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的伤痕和他们太多像似,而且,我们的伤痕在经历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之后大有“旧伤未愈又要添新伤”的态势。也许是他最难的时候吧,与妻子离婚,作品没人欣赏,也没人愿意出版,整天被迫接一些记者的活,写一些自己不愿意写的文章,贫困潦倒,为了给女儿买洋娃娃而去做走私生意赚钱。虽然经常出入文艺圈的聚会,可是相互欣赏能聊得来的人极少,处于人群中却十分孤独,看见不得志的作家自杀,经常做一些奇怪的梦。感觉人生没有出路,甚至考虑放弃写作。后来他移民美国,作品得到非常多的人的认可和喜欢,可惜他才48岁就去世了,直到死前他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有人喜欢。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自己的一生只不过是个可怜的潦倒作家而已。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文化管控下:一方面是艺术家对自我的认同坚持,互相之间未必认同但互相尊重;文豪们打下的基础,让当下艺术家有所坚持,被集体利用的丑态百出。另一方面是艺术家的生活状态,男主视线一直在四处游移观察(包括聊重要事情时),对女性表现出明显兴趣但并未出手,观察者也许疏于、甚至畏惧表态,直到最后鼓起勇气骂了编辑众人;对同事和朋友的若即若离,是只对艺术负责的状态,对现实忽近忽远,游离于想象与责任之间;一直记得女儿的大玩偶,唯一放不下的现实层面借前苏联七十年代作家之口致敬曼德尔施坦姆,布罗茨基,纳博科夫,甚至PinkFloyd的摇滚。一个微妙的细节是苏联右派所感兴趣的与之接壤的芬兰,成了他们了解资本主义阵营的一个窗口。作家艺术家群体生存之困,在全世界都有共通性,正如片中布罗茨基所说:”梵高死得凄惨,国家给不给出版有什么区别呢“。但在前苏联又有审查机制的独特性。”文学不能分为积极与消极,它只有存在与否之分。”“籍籍无名却坚持自我,你知道这需要多大勇气吗?”在噤若寒蝉的年代,如何保持心口如一地书写,如何守住内心最后一道捍卫自我尊严的防线,如何绕开重重屏障保存唯一幸存的语言?1971年,需要典型“英雄”的年代,二战结束25年后的蚀骨重见天日,一切不可言说,一切皆有伟光正航标引领。氤氲色调疏离孤寂,穿行在室内的灵活调度,切切嘈嘈的众声喧哗,他如无名幽灵般游荡在各国家机器门口,这是一个失去身份标识的流亡者,却坚持终身以俄语写作,一切终将过去,他们最终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如同那个冬天的节日般煎熬。“丧”的人注定无法加入你们的赞美,他只是在描写世界本身,想不到竟然有现实意义。多甫拉托夫是冷静的观察者,践行着思考的英雄主义。加入二战的影子、死亡的冲击都不过是平淡中的一点波澜,回到的还是不断前进但又似乎卡壳的时间本身,最终还是无法妥协,最终还是没有买到娃娃,那短暂又漫长的几天被氤氲围绕,一如他的梦境,真实又荒诞,挣扎着醒过来,你看到的还是当下的困顿。梦见被斯大林捕。哈尔姆斯的死亡愚拙得可怕。儿童文学需求不断。有些书离校后读更好。没读过也不喜欢勃洛克。写篇宣言吧。但宣言不是艺术。移民害怕一切。您的作品里没有英雄。面对满地废纸纪念作者。这词听上去很小市民。文学没有积极消极之分。偷进博物馆游荡一夜。如果我的使命并非斗争。地狱是我们自己。布罗茨基一直说不想走。在涉及命运的事件中,大娃娃是重要的目的。愤怒平息后,他困倦地靠在墙上。 [收起]